与其说这是一本访谈集,不如说它是一本对话实录。
访谈者似乎并未存了闪避的心思,“心下先自怯了”,隐身在一杯清茶的淡香里,或者,枉自随着访谈对象的机锋,随风摇摆,却忘记了最初的发愿。这本集子中的访谈者往往更愿意在发问中求证、在交流中质疑、在对话中表达见解,“见解”云者,并不仅仅如习惯理解的那样,纯属访谈对象的见解,而是谈话双方经由砥砺之后共同达成的精神成果。
也因此,这本《见解》(燕舞著,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2年3月第1版)读来颇不轻松,往往需要打起精神,悉心寻绎,才能跟得上书里面那些海内外文化人,还有访谈人燕舞的思路。“深度访谈”云云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读者需要从谈话双方的试探、交集、冲撞乃至背反中,触摸到潜隐在话语下面的思想的流淌。熟悉每一朵云已属不易,何况,还要面对云朵之间的交汇。
不过,惟其如此,这一趟阅读之旅也才具有某种令人会心的愉悦。面对韩少功、查建英、洁尘、张鸣、吴思、雷颐、王明珂、周志文、陈丹青、蔡国强、喻红、潘鸣啸、刘香成、闾丘露薇等一串长长的、晶亮的名字,从人性的本质出发,我们确实可能愿意放低姿态,服膺雅言;却也可能抛出一些挑剔的眼神,打量、审视乃至质疑。而当我们发现,访谈人燕舞其实正是在做着这样一种艰难的努力,不免欣欣然。
就姿态而言,燕舞的访谈是平等的。这种平等建立在对文化、对文化人的尊重之上,既非仰视,更无妄言,呈现出来的只是沉静之美、知性之美。平等云云,往往知易行难,在很多人那里,也就是口头上的一种大言而已。特别是在某些看似掌握了媒体权力的人那里,强权、控制的欲望往往不可遏止,动辄就会流露出来,强迫受访者顺着自己的意志说话。这些年来,类似的访谈并不鲜见。
在这本《见解》中,我们看到的是基于学问、人性、理想的意见表达。访谈者固然怀有“发掘”、“引领”的宏愿,但这种宏愿并不是僵硬、霸蛮地要求得到回应,而是构建起一个平和的、愉悦的谈话氛围,吸引受访者说出一番深深浅浅的道理来。谈话的双方,或许有言语、意见的冲撞,但那不过是在寻找表达的边界而已。这种思想的乐趣同样也传递给读者,原来谈话可以如此美丽。
在对洁尘、吴思、雷颐、蔡国强等人的访谈中,均可感受到这种枝叶纷披、意趣横生的美丽。比如,洁尘说,“整本《提笔就老》,有些地方难免有些八卦。八卦实际上是人性的东西,蛮好的,至少可以让读者比较会心”;雷颐说,“文化的复兴、繁荣不在于有多少钱,在于有一个宽松的环境,大家互相探讨,各种观点交流、冲击、批评、反驳、争论”;又比如,蔡国强说,“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,其实自己还是自己,从农民身上也可以看到我自己追求寂寞的心境。”类似的话语随处可见,读来自是多有会心。
就内容而言,燕舞的访谈是扎实的。这种扎实建立在对访谈对象、讨论话题的充分了解之上,因为案头工作扎实,所以访谈往往能够呈现出杂花生树的绚烂之姿;因为了解对方的为学从艺脉络,所以访谈往往具有令人沉吟徘徊的历史感。如果说,表面上的姿态平等还比较容易做到,这种内涵的沉稳则殊为不易,往往能够在打动受访者的同时,触动旁观的人众。
在《韩少功: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》这则访谈中,我明显感觉到燕舞与韩少功平和谈话背后的机锋。这些年来,韩少功从言语到行动均表现出对农民、对山野的好感,这些都集中表现在他的《山南水北》里面,不过,燕舞却发现韩少功言行之间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悖论,“全书(《山南水北》)只有少数篇幅谈到农民可能有的劣根性,比如附近村民把您买来的青砖‘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’。《拍眼珠及其他》中,您对这种残酷的私刑似乎批判得也不够。您对当地农民的这种好感容易让人联想起‘反智主义’或者‘民粹主义’这样的大词。”这个问题,其实已经无需回答,因为答案就在问题里面。
果然,韩少功以反问来回答:“第一,城里人或上流社会是否就没有劣根性?第二,对有所谓劣根性的人是否就不能有“好感”?比如梁山好汉,是否只配狠批猛揭?第三,如果说农民有劣根性,其原因是否全在农民自身?来自强势阶层的压迫、盘剥、潮流性洗脑等是否也值得审视?第四,如果这些审视都从人们的眼里漏掉和删除,那么批判会不会变味?会不会只是满足上流人自我精神优越感的一种嘲弄和歧视?最后一个小问题:作者的每本书是否都得以揭恶批丑为主题?……”
且不论对话双方的是非对错,仅仅从讨论的题旨上看,此种激烈的意见冲撞显然好看、意味深长。或者这一问题本无所谓是非,谈话双方的表达已经足以让人品味了。
舍此之外,这本《见解》引人瞩目的还有对那些文化幽人的访问。“空山松子落,幽人应未眠”,周志文就属于这样一枚被热闹遗忘的松子。朱天文说,深情人是幽人,就像周志文。诚哉斯言,这位台湾大学的退休教授为人和为文都极为低调,“去除了所有的矫饰与层累之后,用最素朴的语言说故事,像一个孩童般捧起碎裂四散的记忆拼图,茫然四顾。”(张瑞芬序周志文《同学少年》语)其笔下诸人,多是不为人知的旧时同学,这样的人或者安静地活着,或者静悄悄地死去,一切都是那么和谐,又是那么愁人。即便忆及台大师友,也只是写了一个最寂寞的张清徽老师。
这样的选择,显然与其对于生命的态度有关。避开世俗的热闹,在寂寞中品味世道人心。在与燕舞谈及幼年赴台后那段难忘的眷村经历时,周志文显然动情得很,他说:“我住过的眷村是个规模小的眷村,这种小的眷村在台湾整个眷村史上也不怎么能沾上边的,但同样有生老病死的消息,有的庄严,有的荒谬,有的既不庄严也不荒谬。”
同样的幽人,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。这位低调、坦率、自称“不大会随机应变”的学者,甚至告诉访问他的燕舞说,“如果访谈做得不好的话,那也是这个被采访的人过于贫乏的缺陷。”这位一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、大部分精力都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洪先生,直到退休前几年才迎来了学术声誉的顶峰。
燕舞自己说,拒绝“追星”,拒绝锦上添花,“祛除和反抗来自媒体与思想文化界的各种遮蔽”,这样的努力令人尊敬。当然,在“名人”与“幽人”之间,其实并无绝对的界限,不可一概而论。以陈丹青和张鸣而言,作者当初访问他们时,两位似乎还没有“名满天下”,而今则完全不同了。其实,只要对话发乎至诚、有见解、有益于世道人心,幽也好、名也好,都无所谓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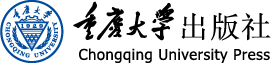

 数字教材
数字教材
 课书房新形态教材
课书房新形态教材
 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