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诗的结构
“摩围寨方圆二十平方公里,三面绝壁,只有迎着安子方向,有一条脊梁转折十八盘下去,一条曲折的石板路绕梁而行……”这就是作者何炬学为其小说《摩围寨》设置的地理环境。由此,小说中的十八个故事有了落地生根的位置和土壤。“摩围寨”,这个毫无疑问是虚构出来的地名,让人联想到舍伍德·安德森的“小城”,乔伊斯的“都柏林”,奈保尔的“米格大街”。这种联想并非因为“摩围寨”与这几个“地方”有什么相似性,而是小说的结构,即《摩围寨》这部囊括十八个故事的小说,在其文本结构上,与《小城畸人》《都柏林人》以及《米格大街》有着一种一致性,即:它们都是发生在同一空间,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结构而成的小说集。
这种结构形式的好处是,可以避开一般“长篇”所要求的一以贯之的故事主轴和逻辑严明的情节罗织,在写作上更加放松和自如,让篇与篇之间可以放心地留下缝隙和空白。但同时,又兼备“长篇”主题一律、人物一律、时空一律等阅读特征,而非杂散、拼凑的“短篇小说集”。当然,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“秘密”是,何炬学曾经是一位诗人,而诗人转写小说,这种如“组诗”般的结构形式无疑是最顺手、最容易掌控和发挥的。这种“诗人化”的偏爱,也从我身边许多诗人兼小说家普遍对《米格大街》表现出的“激赏”之情可资印证。
乌托邦之地
众所周知,所有类型的小说均离不开三大基本要素:时间、空间和虚构。关于《摩围寨》这部小说的空间,前面已经说明,是在一个“三面绝壁”的高寒村寨之内。这种限制性的叙事空间,构成了小说的“封闭世界”,使虚构故事有了一个“实在”的处所,为故事的营造、展开及其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环境依据。
而这个“空间”要素里,自然也包含了“虚构”的要素。作者一方面在小说的“序”中引用了清代咸丰年间编撰的《彭水县志》:“彭水城有山,临乌江而控贵州,高可触天,冰雪晶莹,半年不化。世有板凳蛮居焉,风俗淳厚,物产丰饶,外人罕至。偶有至者,则居而忘返。时日延宕,寨子繁大,土著与流民杂处,相得无碍。板凳蛮呼天为围,故山下人名此山曰:摩围。”这种“博尔赫斯式”的笔法似乎在强调,小说的发生地“摩围寨”是“实有”的。
但是,小说作者又在最后的“跋”中透露:“在广大农村处于普遍贫困、愚昧、争斗的时代,有没有一个地方保有人们希求的那一点点温情、自足、和慰藉?我希望有。而且,我坚信确实有在某个特别的地方,隐秘地存在着。这就是我写《摩围寨》的出发点。或者,我用这样的方式,寻找这样一个地方。”这又向读者表明,“摩围寨”并非“实有”,而是作者为寄托自己的某种理想而虚构(“寻找”到)的一个地方。
有迹可循的时间
再说时间。小说的“时间”分“叙述时间”与“现实时间”两种。如前面所说,《摩围寨》作为一部由相对独立,又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结构而成的小说集,其叙述时间是“非线性”的,而是由十八个“线头”汇集起来的“时间束”式的叙述。
而小说的现实时间,也即“时代背景”,虽然在小说的正文中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交待,但只要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,从其字里行间,如:“那个年代,山下的人有太多的事情要忙。他们忙着如何组织一个派别,向所有敢于蔑视其正确者发动攻击。从文字的口诛笔伐,到武力的刀枪棍棒。一场沸腾着的内乱如同茅坑里翻滚的粪蛆,一团团,一网网,一浪浪,你咬我,我咬你,好不热闹而荒诞”等比喻和隐喻式的叙述中,即可判断出小说的现实时间(即时代背景)是在“解放后”到“文革”发生的那个时间段。
而作者最后在“跋”中也直接证实了读者的这个判断:“对于中国乡村,1950年代到1970年代,是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。从历史的长河看,短之乎也。可是,从这个年代过来的人,每每提到这三十年(1949年至1979年本文作者注),还是难免心紧而惶惑”。《摩围寨》在这个“现实时间”之上,展开其故事与人物的“虚构”,故意不在其叙述中确指小说的“时代背景”,这种故意的“模糊”,一是为了避开“实写”而可能出现的偏差、疏漏和局限,二是其文本结构以及叙述语言的需要,即:相对独立的短篇无法承受三十年历史的宏大架构;简约、诗意的叙述语言与沉重历史的天然冲突要求作者对“现实”采取“虚化”的处理。
非虚构的人性
有了以上对《摩围寨》这部小说在叙述空间与叙述时间上的梳理,接下来我想着重谈谈“虚构”这一要素在这部小说中是如何起到呈现和深化“中心思想”的作用的。
首先,要找出这部小说的“中心思想”。通读完小说的十八个故事,我认为,其“中心思想”可以概括为:以虚构世界的善良与诚实,反衬和反思现实世界的邪恶与虚假,从而为人性确立一个并非虚构的存在。
为了实现这一主题与宗旨,作者避开充满争斗、迫害和荒诞的现实,而虚构出一个“天上的寨子”,即“摩围寨”,书写生活在这个“寨子”中的人朴实、善良、智慧、勤劳的人性之美。而我们知道,在那个“特殊年代”,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无一例外的被裹挟于“政治运动”之中,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和打击。
因此,构成小说的十八个故事,每一个故事基本上都不可能是从“现实”中“采风”而得,而是作者基于前述的“主题与宗旨”虚构而成。如开头的两篇:《巴蛮子》和《老花椒的手艺》,从故事形态上看,都不可能有“现实”的素材和摹本,纯属作者理想主义式的“文学灵感”。《巴蛮子》一篇,通过讲述一个替父复仇的杀手来到摩围寨,因其与寨子的人朝夕相处,获得某种“发现”,最终放弃复仇的故事;以及《老花椒的手艺》一篇,通过讲述一个名叫老花椒的摩围寨人,在离开摩围寨三年之后,突然回返摩围寨,因其秘而不宣的“手艺”让人刮目相看。后来,当其“手艺”(盗牛贼)败露之后,摩围寨人由不相信、愤怒、调查核实到最终包容的过程,皆充分体现了摩围寨人与人为善,得理饶人的品性。同时,也为营造摩围寨这个“天上的寨子”,或曰“世外桃源”确立了底色与基调。
在十八个故事中,我认为最充分体现整部小说的“主题与宗旨”,即“中心思想”的是《赌博之年》和《清查〈康熙字典〉》两篇。
几年前,我曾在一篇比较奈保尔与沈从文的文章中谈到,同样是背井离乡的作家,在书写故乡的时候,奈保尔的“印度三部曲”着笔点在印度现实社会的阴暗面、落后面,行文中充满了对印度国民性的批判。而沈从文的“湘西系列”却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片田园牧歌似的场景,是对湘西土著居民的淳朴民风和良善人性的歌颂。
而我们知道,就在沈从文开始写作“湘西系列”的时期,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,湘西也绝非安宁之地。加上清末民初的国内政治动荡,道德与法制均出现颓败与瓦解之势,全中国难寻一片净土,湘西也概莫能外。但沈从文为何要如此“虚构”出一个文学的湘西?我想,就其写作的“旨意”而言,前面我对《摩围寨》的“中心思想”的提炼,同样可以用来回答沈从文如此“虚构”的用心所在,即“为人性确立一个并非虚构的存在”。而且,在我看来,也可以这样说,作为后辈的苗族作家,何炬学以如此视角写作《摩围寨》,亦有向这位前辈苗族作家致敬之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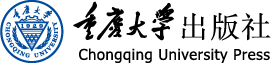

 数字教材
数字教材
 课书房新形态教材
课书房新形态教材
 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