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托马斯这里,神、上帝与其说是宗教意义上的概念,不如说是精神的真实存在的隐喻,它无名、无形,人生而有之,却被文明熏染以至于遮蔽。托马斯以一场战斗隐喻对它的寻找。
如果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诗歌依然能够打动我们,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追究“翻译中流失的那一部分”?诗歌中歌唱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稍有借助,就能显身,对那渴望听到灵魂的声音的人显身。R.S.托马斯的诗歌就是这样。坦率地说,R.S.托马斯的诗歌,打动我的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怀,那种在他者的激励下抵抗的写作策略,抑或是对僵死的宗教仪式的反动。抛开那些复杂的历史的纠葛,不管诗人固执的个人情感取向,托马斯的诗歌仍然能够让我感动,是因为他诗歌中强悍的精神坚执和敏锐地言说。
也许,神学的训练和牧师的职业,决定了托马斯的诗歌对人的精神层面执着观察和深刻洞悉。但我想,更为重要的是,他对个体生命的谛视和追问,对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和作为自然之子之间的恒久矛盾的直面。
翻开诗集的上部,扑面而来的是威尔士乡村气息,泥土、树、农民、庄稼、劳作、鸟、孩子、农妇、风、牲畜……构筑了托马斯笔下普里瑟赫这个虚构的人物所居住的世界。这个世界让我记起韩东的诗句:“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”。不同的是,韩东的诗句是城市生活语境中的回眸,多少伤感、多少抗拒隐含其间,而托马斯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,他以乡村为题材的诗作中,除了“温柔的部分”,还有特别坚硬的存在。这存在既是愈合诗人心灵创口的“记忆深处青春鲜亮的色彩”(《牧师》),也是“岁月潮湿的手/忙着在墙上/涂写字迹模糊的/憎恨与惧怕”。(《山区人口减少》)。在某种程度上,可以说托马斯将所有的心灵图景都编织进他的乡土世界。
前不久在我和同事们举办的一个读书会上,谈论芒福德的《城市文化》时,有学生问为什么芒福德对文艺复兴后的城市给予激烈的批判,而对中世纪的城市充满怀念,按说中世纪是更为缺少人的关怀的时代,而文艺复兴恰恰是人的解放的时代。我当时很想向她推荐托马斯的诗。在某种意义上,芒福德与托马斯的心是相通的,那就是文明的批判往往是从对线性的、进化论似的思维开始,科学技术的进步、发展并不总是意味着人文情怀和道德风尚的同步。对自然和文明的紧张关系异常敏锐且看起来很是保守地呵护着前者,这似乎是浪漫诗人的天然禀赋,在童年与成人、乡村与城市、农业与工业、勤俭自足与商业消费的对立中,浪漫的诗人永远站在前者的一边,从血液里涌出乡愁,在言辞间充满抗议,于无可逆挽的文明前行中,抚摸文明的进程遗下的累累伤痕。
在这样的抚摸中,诗人永远回视返听内心的节律。正如托马斯在一首诗中写神对人说:“我是燃烧的灌木丛/在你存在的中心;你必须/脱去知识/光着思想/来我这……”(《调解》)这里的神,指向的不是彼岸世界,而是内心的真实存在。有时候,诗人甚至更为直接地呈现出充满反讽意味的现代性景观:“太阳沉落时/灯火照亮无数/实验室,科学家们试图/将心灵的黑暗变成知识的白昼”(《历史》)。虽然,在西方世界,科技的凯旋甚至也往往归功于神的创造,当电报发明时,世界上第一份电报稿即是“主啊,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”。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有目共睹,人们享用着科学发明的成果,但同时却远离精神的真实存在,远离那本来居住于人心深处的神。对此,托马斯在《电话》中讽喻道:“电话是智慧树上的/果实。我们可以打给/每个人,但不能打给上帝”。
于是,我们看到,在托马斯这里,神、上帝与其说是宗教意义上的概念,不如说是精神的真实存在的隐喻,它无名、无形,人生而有之,却被文明熏染以至于遮蔽。托马斯以一场战斗隐喻对它的寻找,在这场战斗中“你未留姓名/就退隐,留下我们护理/我们的瘀伤,我们的脱臼”,最终“我们死了,死于/明白你的阻击/在那伟大诗篇的前线永无休止”(《战斗》),这不啻是另一种去魅与去蔽,一种与现代性目标逆向而行的精神格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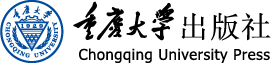

 数字教材
数字教材
 课书房新形态教材
课书房新形态教材
 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
